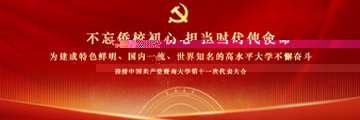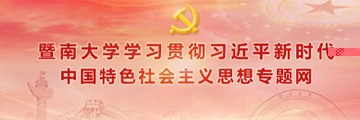醫案一
歐陽某,男,57歲,2022年5月17日初診。
主訴:肢體乏力1年餘。
現病史:患者于2020-08-26,因“蛛網膜下腔并腦室出血”在外院行“引流”治療,具體診療過程不詳。經治療後,患者仍遺留認知障礙,記憶力減退,四肢乏力,雙側小腿甚,行走困難。為進一步診治,求診于楊教授門診,刻下症見:患者認知障礙,四肢乏力,睡眠欠佳,易醒,醒後不容易入睡,飲食可,大便秘結,4至5日一行。體格檢查:血壓不穩定,波動在170-90/95-60mmHg。言語、吞咽功能正常,雙側足下垂,雙側小腿肌肉明顯萎縮,其舌淡,苔黃膩,脈沉細弱。既往史:高血壓病史多年。
中醫診斷:中風;痰濕中阻,瘀血阻絡證。
西醫診斷:腦出血後遺症。
治法:化痰熄風,活血祛瘀,兼健脾祛濕。
處方:陳皮10g,姜半夏10g,茯苓15g,枳實15g,竹茹10g,蒼術10g,郁金10g,川芎15g,丹參30g,粉葛30g,杏仁15g,決明子30g,桃仁15g,姜黃15g,制首烏15g,天麻15g,紅花10g,黃芪30g,膽南星 10g,赤芍15g,全蠍10g,石菖蒲15g。7劑,水煎,口服。
2022年5月24日二診:患者諸症減輕,睡眠改善,血壓穩定,仍訴雙下肢乏力,大便3日1行。舌淡,苔黃膩,脈沉細弱。處方:原方加制遠志、火麻仁。14劑,水煎,口服。
随後,患者多次就診,症狀逐漸好轉。守前方加減,前後予60劑,水煎,口服。
2022年8月16日三診:肢體乏力明顯減輕,行走如常,認知障礙逐漸緩解。納眠可,二便調。其舌質淡紅,苔白,脈弱。以參苓白術散加減善後。
按語:楊教授認為,腦出血屬中醫“中風”病範疇,基本病機為痰瘀阻絡,肝風内動、正氣虧虛,治療以扶正祛邪為基本大法。臨證需辨明濕、痰、瘀、虛孰輕孰重,處方随證加減。初診中見患者認知障礙、記憶力下降,為痰濁擾心,心膽氣虛,結合舌脈,辨證屬正虛痰實;又患者四肢肌力下降及肌肉萎縮,肝主筋,脾主肉,中焦土灌四傍,又主四肢,痰濕阻遏肝脾,則筋與肉俱損;便秘亦提示中焦病變。
本案楊教授采用溫膽湯合二陳湯加減,方中半夏、白術、茯苓、黃芪祛濕燥痰、健脾益氣;枳實、陳皮、蒼術、杏仁破滞散結、行氣化痰;郁金、竹茹、膽南星清熱祛痰;天麻、全蠍平肝熄風、祛風通絡;石菖蒲豁痰開竅;丹參養心通脈;姜黃、赤芍、川芎、桃仁、紅花活血祛瘀;粉葛升清陽、舒筋脈,《本草綱目》:“葛根乃陽明經藥,兼入脾經,脾主肌肉”,故益肌肉。制首烏填補肝腎,濡養精血;甘草調和諸藥。諸藥清熱平肝、益氣健脾、祛痰活血通竅之功。
便秘是中風後遺症常見症狀之一,盲目長期的使用瀉下藥,會進一步導緻陽氣虧虛、菌群失調,因而加重便秘,故治療便秘,攻下治标勿忘辨證求本。除遣方用藥外,重視對患者健康教育,控制血壓、血糖是預防控制腦血管病變的要點,中藥可同時配合降壓藥、降糖藥,教導患者進行适度體育鍛煉以達到更好的控制效果。
鄭重申明:由于每個人的體質和病情不同,本案中的方藥和劑量僅适用于本案病人當時的病情。未經中醫辨證診治,不得照搬使用本案中的處方和劑量。廣大讀者如有需要,應前往正規醫院診治,以免贻誤病情。
醫案二
李某某,男,57歲,2011年10月21日初診。
主訴:左側肢體乏力1年餘。
現病史:患者1年餘前曾因突發左側肢體乏力,在外院确診為腦梗死,經救治(具體診療過程不詳)後,遺留左側肢體稍乏力,5周前左側肢體乏力加重,在外院住院,診斷急性腦梗死,病情穩定後出院,遺留左側肢體乏力較前加重,為進一步診治,求診于楊教授門診,刻診:患者左側肢體乏力,精神萎靡,頭暈,言語含糊欠不清,喉中有痰,色黃,納可,睡眠差,大便幹結,查體:BP150/90mmHg,口角向右歪斜,左側鼻唇溝變淺,伸舌右歪,左側上下肢體肌力IV級,深淺感覺減弱,其舌質紅苔黃薄膩,脈弦滑。
中醫診斷:中風;痰瘀互結挾熱,經脈不利證。
西醫診斷:腦梗死恢複期。
治法:潛陽熄風,祛瘀化痰, 通絡開竅。
處方:白芍20g,生地30g,天冬10g,玄參15g,龜甲20g(先煎),珍珠母30g(先煎),川牛膝15g、天麻15g,鈎藤20g(後下),丹參30g,銀杏葉15g,廣郁金、瓜蒌仁各15g,僵蠶、地龍、桔梗、石菖蒲、遠志各10g,虎杖30g,決明子30g。7劑,水煎,口服。
中成藥:血塞通軟膠囊,每次2粒,每日三次,口服。
二診:左側肢體乏力稍減輕,頭暈減輕,睡眠明顯好轉,大便已通,喉中痰消,餘症亦有所減輕。其舌質淡紅,苔白略膩,脈弦。上方去桔梗、瓜蒌仁、決明子,加全蠍5g,水蛭5g,烏梢蛇10g。30劑,水煎内服。中成藥:血塞通軟膠囊每次2粒,每日三次,口服。
三診:上下肢肌力基本恢複正常,患者微笑時口角輕微偏斜,頭暈消除,語言清晰,精神疲憊亦明顯改善。處方:上方加減進退以善其後;囑托:日常注意保持情緒穩定和重視飲食起居,以防病情反複。
按語:楊教授認為,中風後遺症往往病情遷延日久,病機複雜,痰瘀互結為基本病機;然患者久病正氣虧虛,故治療時以扶正祛邪為基本治法,随證加減用藥。根據本證的臨床症狀和舌脈,辨證為痰瘀挾熱,阻塞清竅,經脈不利。組方上,患者患病較久,正氣已怠,病邪根深蒂固,須投以重劑,為求“重劑起沉疴”之效。
該患者同時伴歪舌、左側肌力、感覺下降,考慮肝風内動,肝經失養,又肝主筋,故配合滋養肝陰,斂陽熄風之法;大便幹亦提示患者陰傷之證。因痰濕與陰傷證治法易互助病邪,故治療處方用藥上需抽絲剝繭,根據髒腑定位,相應攻補兼施。
本案楊教授取一貫煎、天麻鈎藤飲方藥加減,白芍、生地、龜甲補斂肝陰;珍珠母、天麻、鈎藤、僵蠶、地龍熄風通絡;玄參、虎杖、廣郁金清熱涼肝、行氣祛濕;丹參、川牛膝活血化瘀;瓜蒌仁、天冬、桔梗、銀杏葉清熱利咽、潤肺化痰;石菖蒲、遠志開竅豁痰、安神益智;決明子清肝熱兼通便;同時配合血塞通中成藥聯合治療。現代藥理研究表明,鈎藤具有降血壓的功效,患者血壓偏高,中西合治,堪稱合拍。二診大便已通,喉中痰去,故去決明子、瓜蒌仁、桔梗;同時,加強方中活血祛風通絡之性,加用全蠍、水蛭、烏梢蛇。三診取得良效,故效不更方,守方繼進。
鄭重申明:由于每個人的體質和病情不同,本案中的方藥和劑量僅适用于本案病人當時的病情。未經中醫辨證診治,不得照搬使用本案中的處方和劑量。廣大讀者如有需要,應前往正規醫院診治,以免贻誤病情。